上野千鹤子 | “近代家庭”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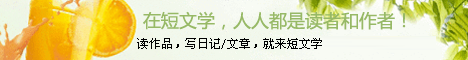

“近代家庭”的形成
上野千鹤子 著,邹韵、薛梅 译
选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近代形成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究竟有没有出现瓦解“家庭”概念(包括传统家庭在内的)的动向呢?针对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理想状态上来看,参与市场这一经济交换游戏的玩家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分离继而成为“自由的个人”,他们“摆脱了生产资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无产劳动者。这里的“个人”,在英国,它是指由于“圈地”而导致被迫离开土地放弃农业的农民,而在日本,它是指土地被长男继承并独占的农业家庭中的次子和老三。对市场而言,参加游戏的“个人”基本上都是单身者,并且“个人”是否进行再生产与市场无关。正因如此,神岛二郎指出,英国在工业化初期时存在着弃农的农业家庭涌人城市的问题,而日本与英国不同,日本实现了“单身者类型”的近代化,只需以“福利立法”的形式,就可以不花毫厘地来维系劳动者家庭。
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掀起的技术革新使劳动的质平均化,这正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r).诸如以时间单价来计算“劳动价值”的说法,其前提是“抽象劳动”的形成,也就是舍去全部劳动的质,将“抽象劳动”作为共同的分母,去除劳动中存在的质的差异并使它们的互相交换成为可能。因此,资本主义中的抽象劳动也一并破坏了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传统劳动中的差异性。就连在技术层面上的工厂生产,都用熟练劳动替换掉了连女性和儿童都能进行的非熟练劳动。总之,以市场为前提的“个人”是不问性别和年龄的“单身者”,而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单身者就是如克隆人般能进行自动再生产的存在,并且不花丝毫的成本!正因如此,这种体制也是最理想的。对于市场式的生产体制而言,作为再生产变量的性别和年龄只会是干扰而已。
至少理想状态下是这样的。但是,家庭史研究以及比较近代化理论逐渐明确的是,在市场化推进的初期,市场化只有在与市场外部这个重要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发展起来。例如,在工厂劳动初期,有许多女人和儿童加入了工厂工人的队伍中,这不仅仅是源于技术革新带来的“非熟练劳动”的普及。女人和儿童成为工厂工人是因为传统社会中对性和年龄的差别对待。即第一,女人和儿童的工资较低;第二,使货币这种不可靠的新型社会资源首次登场的是这样一批人,也就是被排除在土地及名誉等传统型社会资源分配之外的人们——女人和儿童以及底层男性。工业革命虽然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无论最初的纺织工人是男人也好,是女人也罢,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传统性别分工残存的影响。纺织这项工作传统上是女性的工作,即使机械化改变了其劳动形态,纺织工业仍旧由女工来承担。但是由于劳动由私人领域转向了公共领域,也就出现了像印度这样的由男性独占机械化劳动的社会。
女性劳动经济史学者千本晓子详尽地调查了明治时期工厂工人的薪酬账本。她证明了不管地域、职业有无差别,无论是哪个工厂,女性工人的薪酬几乎都被控制在男性工人薪酬的三分之二左右[千本,1981].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的职位不同(男性工人负责监督女性工人),而这一点却无法从劳动的内在原因中得到相关解释。但是,这个薪酬控制的过程,是以锯齿形的方式向男女同薪同酬趋近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徘徊,即附着于传统社会的“外部”且逐渐膨胀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于如何应对市场外部的因素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
哈雷雯(Tamara K.Hareven)用庞大的社会史资料证明了就连工厂工人的招募都没有瓦解家庭制度,反而还利用了家庭的联系[Hareven,1982]。从叔叔到侄女、从姐姐到妹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一并被雇用为工厂工人。就连在机械化工厂劳动的队伍中,都存在着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也就是父亲监督着女儿、姐姐与妹妹共同劳动。家庭式关系可以说被照搬到了工厂劳动的队伍中去。家庭劳动团队由农田那片土地转移到了工厂这片土地上。
在资产阶级式近代家庭的理念尚未瓦解前近代式家庭一经营体之前,工业化急速地发展,这一阶段的家庭—经营体的理念往往只是通过“放弃农田”来实现的。简单来说,就是出现了诸如工业化进程越晚,女性就越容易进入职场工作的悖论。即便是在日本,与城市相比,一般来说在农村的女性的就业率更高,她们对工作的抵抗也更少。只要“家庭劳动团队”的传统仍根深蒂固,无论是女性还是儿童,只要是能工作的人,但凡有机会从事劳动,他们的劳动就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之事。鹤见良行周游亚洲,他发现无论是儿童、女性,还是老人,甚至是一家之主,都做着无法自足的收入微薄的工作,拼拼凑凑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对此,日本人可能会感到“悲惨”,而对于他们这种看法,鹤见则敦促他们进行反思[鹤见,1986].鹤见提醒道:“细细想来,前近代社会的生活不就是老人和年轻人都通过各自的劳动来维系着全家吗?”对于有着“家庭劳动团队”意识的人们而言,近代化只不过意味着劳动形态由非货币领域转向了货币领域而已。
村上信彦也在《明治女性史》[村上,1977]中指出,明治时期,最初在工厂劳动的工人是通勤女工,而她们中的多数是已婚者。而像《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寄住在雇主家里的未婚女性劳动者,她们之所以是“女工”的主力,是因为日本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完成了工业革命,其纺织业飞跃发展的过程要求劳动的强化。与已婚的通勤女工相比,未婚、单身以及寄住在雇主家的女性劳动者要忍受低薪且更长时间的劳动,她们处于更容易被管理的环境。通勤女工将家庭问题带到了劳动之中,另外,她们总是有很多的牢骚和不满,而且她们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不受雇主的欢迎。
从已婚的通勤女工到未婚的女性劳动者,劳动者变为超越了性别和年龄的单身者,这当中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结果。然而,她们只有在进入劳动市场之时才是“自由的个体”。实际上她们仍然只是父权制之下父亲所持有的财产般的存在,靠着提前支付的微薄的薪金到工厂打一整年的工,而她们还只是年幼的女孩子。她们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置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决定权,并且无法取得劳动的收益。父权制下家庭财产权的支配对象不仅有女性,还有孩子。我们常常关注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和剥削,而容易忽略父亲对女儿的剥削。日本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贯彻市场原理做到的,而是市场通过抓住父权制这一市场外部原理趁虚而入建立起来的。
虽说如此,由于家庭式的劳动从非货币领域转移至货币领域,这使得旧制度下的家庭权力机制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是因为劳动的货币报酬是归属于个人的。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很难分清劳动成果的个人归属。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均按照权威的分配结构而被置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无论女性劳动的贡献有多大,也未必会与劳动生产物的所有权相结合,正因如此,它与女性地位并无关联。然而工厂生产之下的男女雇佣工人会以薪金的方式来明确个人劳动成果的归属。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的独裁所有权。
然而这也是要建立在“个人”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家庭”这一单位作为超个人的实体这种观念已经被内在化,而个人不过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已,因此劳动者的薪酬不归属于个人。譬如父母代替子女受领预支工资,丈夫去妻子工作处要求预支薪水等。从这些司空见惯的行为来看,劳动者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并非作为“自由的个人”在工作。即便劳动者个人按照自由意志来工作,比如在外工作的姐姐给大学在读的弟弟寄送生活费或者供养乡下的弟弟妹妹,这不是由于制度的强迫,而是将家庭内在化的结果。她们作为超个人实体、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在劳动。这无法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而是家庭外部的,且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
货币经济依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的渗透在时间上存在延迟,这对于传统家族内部权力机制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显著。比如,长老独占了传统的贵重财产,而对于货币这种不太可靠的新型财产,保守的长老则会拒绝。因此,对于在“结构上处于劣势”(structural inferiority,特纳语)的女人和年轻人来说,货币反而是更容易入手的资源。在交换经济上鼎鼎有名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当岛上传统经济被卷入“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语)之后,人类学家就货币经济化的进程进行了众多个案研究。其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货币经济化对传统社会的威信构造(authority structure)产生了威胁。在传统中,被称之为库拉环的有关荣誉的交换游戏之中不包括女人和年轻人。然而他们通过掌握新技术(开货车)或通过教育这一方法(学校的教师)获得了货币收入。随着货币这一新的社会资源逐渐可以交换罐头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业制品,这表明了货币是一种流通性较高的媒介,传统贵重财产的威信则随之降低。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走出岛外工作赚钱的女儿和儿子,将获得的现金收人汇给家里人,虽然这些现金仍然被看作是参与传统交换游戏的父亲、叔伯的贵重财产,但女儿和儿子被公认为拥有实质的所有权。[Gregory,1982]
这也是市场外部的要因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是过渡期的悖论。在社会的变动期之中,通常来看,原有的旧秩序之中的受益人反而最无法追随变动的浪潮。然而这种“时差”的消除,正如字面意思一样,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当社会构成的成员全部转移到新秩序之中后,这种过渡期的逆转就会消失。如此一来,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间,男女薪酬差异大约固定在了三比二的比率上,而未婚女子劳动市场也相继成立了。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雇用男性家长劳动者、清除劳动市场中的已婚女性,这种“结婚了就做主妇”的常识沿着Z字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通过引入并利用市场外部的要因,在资本主义初期就逐渐形成了这种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处理市场外部的要因呢?在这一反复试验的过程中,比如在自发形成了资本主义并推动其逐渐走向成熟的英国,它的发展更加具有戏剧性。通过“圈地”而使得被迫放弃农业的农民举家迁至城市,这使得城市的移民承受了城市病症的重担,他们在面临着贫困、犯罪、卖淫、疾病、贫民窟化等各种城市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家庭解体的危机。对于城市的怨恨是源于城市移民的生活现实。针对这种现实,16世纪到17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济贫法。据说济贫法是福利立法的原型,从济贫法的成立过程来看,所谓“福利国家化是在后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的”这种发展阶段论说是值得怀疑的。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制度成立极早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可以说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充物出现的。自由市场虽然理应要求国家的最小限度,但实际上,市场从最初便针对“外部”向国家提出了要求。看上去,市场仿佛最初便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即市场仿佛提前预测好了一样,若将市场原理合乎逻辑地极限化反而会增加干扰而陷人悖论。
1802年,英国制定了最早的工厂法案。它规定了禁止9岁以下的少年参加劳动,9到13岁的少年劳动时间被限制在每周48小时之内,等等,因此它又被称为最早的劳动者保护法。这一劳动者保护政策进而又由少年劳动扩展到妇女劳动。这些针对妇女、少年劳动者的“保护”立法,最终给劳动市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是女人、儿童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这导致了成人一男性劳动者独占了劳动市场,以及男性背后的“女人和儿童的世界”脱离出了劳动市场。倘若不考虑脱离出劳动市场的“女人和儿童的世界”,那么“母爱”和被保护的“儿童时代”的概念就无法成立。
劳动市场驱赶女性、孩子而仅对成人一男性劳动者开放,这究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否是划算的买卖仍是疑问。这是因为成人一男性劳动者还并非“自由的个人”,实际上他们当时仍是作为家长劳动者的家庭代理人。如果成人一男性劳动者是“自由的个人”,那么只针对这一单身者的再生产,市场支付相应的成本作为其劳动报酬理应足够了,但事实上,当时资本家家长劳动者支付了其足以扶养家庭的薪酬(即便这只是最低限度的)作为“家庭津贴”或者“生活津贴”。这从市场原理来看的确是干扰①。
家长一个人代替了所有家庭成员成为“顶梁柱”(breadwinner),只要他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得到养活一家人的薪酬,而也有人将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进步”。相比于全家劳动时代下家庭成员的总劳动时间,家长劳动者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或许较短。这也是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结果。虽然“生产劳动”的时间减少了,然而对于被隔离在“家庭内部领域”中的女性和孩子而言,等待他们的则是“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与“被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女性和孩子”的隔离使得孩童时代延长,这与长大成人所需要时间的延长密不可分。在前近代社会之中,9岁的少年就拥有了足以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被禁止劳动的少年们被迫接受教育。孩童时代的延长意味着教育时间的延长。与此同时,教育的作用就是将等级(grade)更高的劳动力输送至下一代的劳动市场。伊利奇(lllich)睿智地将“(接受)教育这一劳动”看作是“影子工作”(shadow work)的一种。教育并非单单是充实自己的活动。为成为一名劳动者而接受教育的孩子们自己承担着这种准备劳动。(接受)教育从其强制性的特点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且这种劳动是被置于非市场领域的无偿劳动,从这两点来看,接受教育这一劳动与“影子工作”有着相同的特点。如果将“女性和孩子”的影子工作也计算在劳动时间之内,并且支付给家长劳动者的薪金还约定俗成地包含这种个人的再生产劳动的话,那么户主单独收入(single income)这种形式的劳动与家庭集体劳动这种形式相比,很难说是一种“进步”。
注 释
① 日本的薪酬结构如下:青年、低学历层呈现的是单身型,而在其结婚年龄前后开始极快地上升,并在中年期呈现停滞状态。支撑这种薪酬体系的理念并非针对个人的“职务津贴”,而是将其生活周期的平均类型作为约定俗成的前提的“生活津贴”体系。
(责任编辑:副主编)相关阅读
最新文章



最新消息
欢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