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述诗歌的炼意,说理精辟,一生至少要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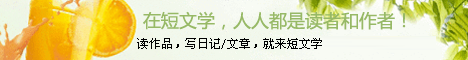

读者们经常会问,写作时到底是炼字重要、还是炼意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炼字和炼意的区别。说起来也很简单,炼字就是要字斟句酌,追求用语贴切、传达精妙。而炼意就是要构思新颖,讲究情意真切、布局精妙。古代很多诗评家都探讨过类似的问题,诗人们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注意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比如杜甫《望岳》中的“一览众山小”,可谓气吞天宇,更显旷达胸襟。明朝末年就有一位学者,也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下面介绍的是王夫之论述诗歌的炼意,说理精辟,一生至少要读一次。
《姜斋诗话》(节选)作者:王夫之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处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自幼跟随父兄读书,青年时期又曾参加反清运动,晚年时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世人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反对宋诗中太过重视说理,反而认为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作者又继承了古典文学的很多优良传统,主张诗歌的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应该相互协调。
《姜斋诗话》是王夫之撰写的谈论诗歌理论的著作,这里选择其中一段描述,说明诗歌创作中立意的重要性。这段文字只有124字,却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作者的观点。王夫之认为,无论诗歌还是文章,必须注意立意。三军如果没有统帅,就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诗歌没有中心思想,读者也就不知其所云。李杜的诗文就非常重视立意,几乎找不到“无意之诗”。
作者举了一些典型的意象,说明写诗就像造房子,没有地基和房梁,就会让风轻易吹倒。意象就是诗文的架构,没有它们,就显得毫无意趣。王夫之又介绍了齐、梁时代的诗文,宋人觉得其非常华美,于是便在其中寻章摘句,却毫无情感,结果就难以跳出前人的框架。这种创作手法得不偿失,最后将完全丧失自己的能力,简直就是一种小家子路数。
其实不止王夫之这样认为,清代的袁枚也曾说,很多人写作时,只要一题到手,必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老生常谈,不召自来。也正如老子所言,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真正的大匠,总是把顽璞凿开,而示人以真玉。作文炼意,就是剥去庸人思路,而示人以深意。当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杂质除、精意现,一篇优秀的诗文就会呼之欲出。
立意讲究两件事,求新和求深。新,就是题材、观点、手段新颖,别出心裁,冠古绝今。深,就是含蓄不露,又耐人咀嚼。一首好诗总能令人一唱三叹,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东风无力百花残,既描写春天的景象,也是义山惆怅心境的反映,不仅构思新,而且立意深,让心灵与自然达到精微的契合。再如李白的《蜀道难》,笔意纵横,豪放洒脱,而其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寓意深远。
清新,即形象新鲜活泼之意。诗人追求的不是孤立、抽象之意,而是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即渗透到形象中的意。诗意与情、景与境密不可分,所以诗人的立意创新,是情景交融的新意境。再如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表现春天的气息,看似并无多少新意。但这种春天气息好像猝然与景相遇、也是不假绳削,所以就显得意新语工。还有苏轼的“浓妆淡抹总相宜”,也具有匠心独运的新意,即使跨域时空,也是愈久愈新,愈淡愈远
相关阅读
最新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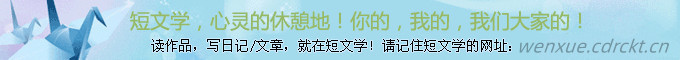
最新消息
欢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