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散文】老院的枣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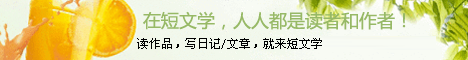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来赶集——说的是秋季次第成熟的三种水果。三者各有各的美味,于我而言,最喜欢的是枣。中秋节快到了,团圆的饭桌上可以没有梨,没有柿子,但枣和月饼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标配”,如果自家蒸的月饼里没有加进枣泥,馍上没有点缀红枣,那肯定是没有灵魂的。
小时候,我家老院子里有一棵枣树,长得枝繁叶茂,春天开满一串串黄色的小花,远远就能闻到馥郁的花香,到了夏天,荫翳蔽日,树下又成了纳凉玩耍的好地方。但我们小孩最盼望的还是秋天,每天上学放学从树下经过,都会下意识抬头看两眼,瞅着枣子小得像米粒,不免有点着急,不知道它们哪天才能长大长熟。
又似乎某一天,忽然感到好几天没有听到蝉的聒噪了,才发现夏天正悄悄溜走,而枣子已由翠绿开始泛白泛黄,进而变红了——吃嘴精们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成熟的大枣像一颗颗肥嘟嘟的玛瑙,黄里透红,饱满鲜亮。生着吃,脆爽多汁;放进粥里煮着吃,软糯香甜;晒干了吃,筋道耐嚼;而我们自创的红枣裹花生,则实现了醇香与甘甜的完美结合,一大口下去,顿觉幸福感爆棚。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在这个丰硕的季节,最兴奋最热闹的就是打枣了。大人们提前在树下铺上笘子、苇席,有时还在上面铺一层被子,防止大枣落地时摔破。父亲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从不同方向叭叭叭地敲打枝干,随着枣叶纷飞,大枣扑腾往下掉,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我们在下面大呼小叫着边拾边吃,枣子砸在头上,也全然不顾。有几个大枣长在树梢,竹竿够不着,我自告奋勇要爬上去摇,但因为枣树高、刺又多,母亲不让我爬,说要留几个枣看树,不能打得那么干净。
我家这棵枣树看上去俊秀挺拔,结出的枣子也是个大肉厚,但枣子结得稀。相比而言,邻居长保家的枣树长得并不高,但树冠很大,枣子稠得把树枝都压弯了,这令我常常羡慕不已。
为了让枣树多结果,我和小伙伴会在腊八节那天,用斧子或菜刀在枣树躯干上砍几个口子,然后用小勺子舀腊八粥喂它,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枣树娘娘喝个饱,枣妮枣娃早报到。”“砍一斧,结石五;砍一刀,结十稍。”石五、十稍到底是多少?并不清楚。砍完我家砍你家,喂完大树喂小树,可到第二年中秋时节,等夜色渐起,月光皎洁,一顿红枣月饼的美餐过后,早把“增产增收”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家里盖瓦房,父亲把老院子里的榆树、杏树和枣树一起伐掉了。榆树又粗又直,毫无悬念地当了大梁,杏树和枣树短粗弯曲,不能做梁,但因为都是硬木,便用大锯解成木板,杏木板做门窗,枣木板则用作门窗的过梁,也算是各得其所。大树无语,和生长在土里时一样,仍默默地迎接每一天的晨露夕照、风吹雨打。而它们带来的童趣,至今还在我心底荡漾
相关阅读
最新文章



最新消息
欢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