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众文化批评应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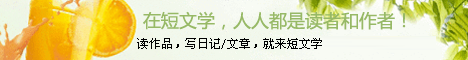

当前大众文化批评应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姚一诺
在文化批评领域重提阶级问题是有必要的,近年国内一批以热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现象,为文化批评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提供了鲜活的分析材料。他山之石可攻玉。美国批评家詹明信曾提出两种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否定阐释学与肯定阐释学,前者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祛魅,后者主张对文化现象进行乌托邦分析。否定与肯定相结合,构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詹明信认为任何文艺和文化批评都需坚持运用双重阐释学。不过,目前中国的大众文化生态,特别是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还不具备向批评提供肯定阐释路径即乌托邦分析的可能,换言之,发现并肯定国产剧、综艺节目中的乌托邦因素不是当下批评的主要任务。
这里仅以两部热播国产剧为例加以说明。2016年播出的《欢乐颂》即是一幕阶级和解的乌托邦。《欢乐颂》中暴露的种种阶级问题,制造的种种阶级和解的幻景和神话,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及策略以应对是必要且有效的。《欢乐颂》颂的是什么?是阶级和解。诚然,剧中也展示了阶级冲突乃至阶级对立,但最终目的是为达到阶级调停,向大众释放阶级调和的讯息甚至制造社会和谐的假象。但事实上,这种阶级和解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一触即破的乌托邦。电视剧向大众呈现这一乌托邦幻觉,不仅是叙事策略的成功实施,而且包含了更深的意识形态考量。
剧中几个主角都是女性,让人不由想起作家张洁的一部小说《方舟》。只是张洁笔下作为女性共同体的乌托邦即“方舟”到了《欢乐颂》,则完全蜕变为对主流价值的膜拜。虽然在小说中,女性共同体最终也是失败的,但它所提供的乌托邦的正面意义绝非《欢乐颂》可比。剧中,将不同阶级、不同出身的女性黏合在一起的,并非性别,而是资本,既包括有形资本,也包括象征资本。也就是说,资本的力量已经超越阶级和性别,成为掩盖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实质的“面纱”。不言自明,资本是当今社会的绝对王者。曾作为具有解放意义的概念“性别”,不可避免地大幅倒退,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究其实,则表明总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或许正在走向其反面。
在《欢乐颂》里,安迪的孤儿出身只是表象,因为实际上她有一个一直未被“发掘”出的极为成功的父亲。安迪和曲筱绡,正是当下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某种想象,分别代表了两种极端,但相反相成。剧中,安迪占据了一切优秀品质,她的缺陷只被认为是其优秀必然付出的代价。曲筱绡则代表了社会对新富阶层或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想象,既厌弃她的肤浅刻薄,又羡慕她的聪明多金。而樊胜美纵有诸多不易,终于也是虚荣和拜金所致。至于邱莹莹这样的城市低阶,虽然生活在上海,却依然是曲筱绡等调笑的对象。可以说,正是由于阶级区隔形成的刻板印象,类似邱莹莹这样的人才被定性为夸张、无脑、从众和可笑。此外,该剧存在大量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大众乐于接受并甘愿追求的价值观念,也充斥着对物质的过度追逐和对所谓上流生活拜物教式的向往,而这些无一例外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常见和最为主流的价值设定。
《欢乐颂》制造了一幕阶级和解的乌托邦幻象,其所呈现的和谐局面并不真实。在大众文化批评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倒退和僵化,而是应对和揭示社会现实之必需。不提出对资本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批判,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便很难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正如英国学者肖恩·霍默所言,阶级与经济“在今天的社会关系中将会表现出比我们以往历史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决定性。因此,詹姆森(詹明信)所给我们的教诲,在关于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某些基本问题上,将比我们愿意接受的更合时宜”。
今年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三十而已》,对阶级问题的呈现更为集中和明确。应该说,每一阶级都不是同质的,阶级内部有不同阶层,同一阶层也面目各异。小企业主当然也是资产者,尽管今天我们很少使用“资产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等语汇。如剧中开烟花公司的许家,他们要想上升和扩大再生产,就须建立各种关系网,不仅仅是能提供再生产的供应商,还有更高阶层的大中型资本家,如剧里的女主角之一顾佳买名包、混太太圈即是一种手段。其实,资产阶级内部既相互鄙视又彼此依赖,如资本家太太们在一起做衣服的场景中,就展示了开始走下坡路的三代实业家,他们以资产阶级中的“贵族”自居,即所谓老资本家,看不起一些新富和暴发户,含酸拈醋,但又不得不同他们合作。顾佳则是想奋力挤进太太圈的人,尽管她厌恶她们的无聊做作、虚伪矫饰,但还是曲意逢迎。她与王太太之间,就属于可互相利用的一对关系。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同时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爱好社交就是其中之一,或者说社交成为一种必需和日常,甚至任务。如果不擅社交,很难真正融入这个阶级。这在剧中有很多表现,例如太太圈、下午茶、游园会、开派对、高尔夫、游轮行等等。顾佳做蛋糕送给王太太,让儿子给幼儿园每个小朋友都送蛋糕,这些都是为了交换,物本身的使用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外,学赛马表明资产阶级在复制已消失的贵族的生活方式,并且资产阶级新富又在模仿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后起的阶级总是会接受和模拟被他们打败的更高阶级的文化,而同一阶级内部的下层则会不断内化上层的意识形态。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上述现象曾在我们国家被视为腐朽和被打破,如今却有复潮之势。历史不会倒流,但会倒退。更可悲的是,它们被那么自然地镶入我们的大众文化,甚至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观。
这部剧的好处是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阶级问题,换句话说,阶级议题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再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消退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问题,但阶级概念从未失效。现在的阶级结构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阶级界限变得更加模糊,阶级构成更加多质,但因跨国资产阶级的联系更为紧密,无产阶级的国际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并且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不减反增。这也表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阶级根本对立的状况依然是现实,只是不像19世纪那样矛盾尖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早已指出,工资是无产阶级内部趋于分化,甚至彼此竞争、倾轧,难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的重要原因。而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
剧中,顾佳想接转茶厂,考虑到无暇顾及儿子,决定请育儿师,为了节省空间和工资成本,她要求保姆必须和育儿师同住,甚至提出要她们睡上下铺。当保姆提出异议时,顾佳不再表现出平日的礼貌亲和,而是一改脸色。这里,阶级意识得到了再现。然而,剧里那些“高级工人”却没有什么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以恪守资本家制定的规则为职业道德,以向资本家投怀送抱为荣,在去阶级意识的同时内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坚决执行资产阶级的剥削政策,甚至协助资产阶级发明新的剥削方法。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入脑入心的集中体现,他们是无产阶级中的上层,但并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还有一个有趣的设定,顾佳和丈夫许幻山经营的是烟花公司,而后顾佳决定兼营茶厂。烟花主要用于娱乐,茶厂毕竟与生产相关。顾佳为何决定拿下远在湖南的茶厂,仅仅是出于欲望和利润动机?这其中是否也暗示了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种隐微变化?顾佳只身去湖南茶乡考察,在村长的迎候和殷勤接待下与茶农(农业工人)见了面。茶农们一见到顾佳,仿佛见到了救世主,异口同声地喊“顾老板好!”就好像顾佳来了,他们的生活马上就能翻天覆地了,顾佳就是村长为他们请来的大救星。顾佳让他们别叫自己老板,直呼其名就行,茶农们又立刻高喊“顾佳好!”连十来岁的小女孩也懂得只要巴结好顾佳,他们就有希望了。看到这些,心里很复杂。现实中的农民见到他们的“老板”时,会和电视剧里一样吗?顾佳还不是投资商,她也是需要拉投资的,她在投资商面前大演善心,把逐利的商业行为表现成情怀使然,这点也让人不适。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传统农民向农业工人全面转化,这些最基层的农业工人可能连他们的大雇主是谁都不知道,更不可能意识到农业资本化必然导致中间层不断增加,而每一层都包含剥削。说这些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评要注意了解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
此外,剧中对顾佳一家和王太太家所住楼层的设置及她们的不同反应,也是一个颇可玩味的细节。顾佳住12层,王太太住21层,顾佳羡慕王太太,回家后对丈夫说,她40岁,我们30,我们努把力,很快就能升到她那个楼层了。这里不妨再引詹明信的一句话以作参考,“在左拉的《家常琐事》中,各个层次的公寓住房,与从一楼的阔绰房客一直到阁楼的女仆和工人的各个社会阶级相对应,因此这样一部作品就是讽喻式的,因为阶级意识仍然于社会本身内部结构上发挥功能:它被包含于内部,作为整个社会的一种地图或图表,作为一种区别性的情感,人们借此确定自己与其他阶级的关系。”
另有人谈及剧中固定出现的煎饼小摊一家,他们的生活充满温情,用以反衬主情节,体现了这部剧的人文关怀。笔者不反对这种阐释,但应注意到,在剧里这一家的所有镜头都是无声的。尽管他们的劳动和生活被摄入了影像,或许让我们感到平凡生活中的点滴和温暖,但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自我阐释的权利。因此,这家人的所有生活场景都是功能性的,他们被树为他者。
(责任编辑:副主编)相关阅读
最新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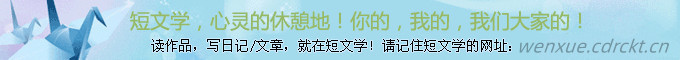
最新消息
欢迎收藏